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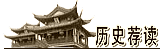 |
读蒋日记者,能不慎乎? |
|
文/汪荣祖 2021年05月20日 来源:《历史评论》2021年第1期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
国人书写日记的习惯,其来甚久,近年大量历史人物日记的问世,毫不意外。传世的日记中,其初衷不在于流传后世的,一般所写较无顾忌;有意传世者,必有顾忌。蒋介石发迹较早,其经历关系到20世纪诸多重大史事,其手写日记由其家属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,2004年向公众开放后,引起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,查阅者络绎于途,欲一探“宝藏”。
蒋介石工作之余勤写日记,在政治人物中虽属罕见,但绝非偶然。自早年起,蒋的行事资料就由其亲信如毛思诚、陈布雷及所谓“奉化三先生”—王宇高、孙诒、袁惠常等人掌管。结合毛思诚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》、陈布雷《蒋介石先生年表》以及《事略稿本》,一直到蒋败退台湾后的“大溪档案”,可见蒋氏的生平资料早已体系化,加之较完整的手写日记,可视为他生平资料体系建设的完成。蒋介石日记在其生前就有专人摘抄,死后由其家属公之于世,都是蒋氏一家之言。若有人说“蒋氏日记是仅供他个人参考的私密空间、无意传世”,则纯属昧于事实。
对于蒋介石“勤于”记录自身言行的行为,正如黄倩茹女士所指出的,古之帝王由别人记载起居注,而蒋由其本人亲写“起居注”,以便日后写“正史”之需。古之史官的实录虽未必尽实,但尚有“天子不观史”的传统;而蒋以自身日记为实录,怎能不令我们对其日记的真实性产生疑虑?黄女士在这里所要提醒的,正是要注意分辨“真实的蒋”(person)与蒋“要我们知道的蒋”(persona)。蒋日记显然是蒋“要我们知道的蒋”,我们如何从日记中读出“真实的蒋”,才是学问。
蒋介石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中心长达数十年,记录他每日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行,当然有参考与引用的价值。日记须及时记一日之事,但即使再有恒心的作者,也不可能一天不漏。后来补记或改写,则有损日记的意义,因敏感议题而涂改,颇有前例,更属等而下之!蒋氏日记有无此等问题呢?有人通览蒋介石日记手稿发现,“蒋先生每每在关键处或予省略或用词含混。因而读此日记,我们应当注意到蒋先生省略掉或没有明白写出来的事项,不能只以日记中的记载为标准”。
蒋氏日记在公开之前,无疑经过家人的编辑与删节,也有黑墨涂抹之处。当蒋氏“大溪档案”移交台北“国史馆”时,笔者听闻“国史馆”负责人提及,“其中缺件甚多,因档案经过秦孝仪的过滤,‘国史馆’皆登录有据,以免负缺件之责”。于此可见,蒋氏的资料包括日记在内,既不完整,也很不真实。我们可举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,互相对照来评判蒋介石的日记。
其一为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。此事件号称是“谜”,根本是蒋在故弄玄虚。他于事件后不久的孙中山纪念周会上演说称,“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,要等到我死了,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,才可以公开出来。那时一切公案,自然可以大白于天下了”。此话即已证明他的日记是要留给后人看的。他的考虑是,事件的秘密藏在他的日记里,当时不能说是因没有人会相信;等他死后,时过境迁,死无对证,其日记所说就成为定案。
其实,1926年3月10日蒋的日记已呈现出其心理状态,如“委屈”、“受辱”、“遭迫害”、“被遣送”,所谓“疑我、谤我、嫉我、诬我、排我、害我”等,无非暗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想要害他,但又提不出任何实证,显然是他为发难找借口而已。事实很清楚,在事件发生之前,蒋介石是汪精卫的手下,但在事件后,蒋即取汪而代之;蒋之所以得逞,是因苏联顾问受斯大林之命,支持蒋“这位红色将军”(苏联档案记—引者注),这导致汪愤而离粤赴法。正基于此,蒋甘冒以下犯上的风险,精心策划了这场大戏,并得其所愿,成为事件的“最大赢家”,可称一场得逞的豪赌。
若将此事件说成“右派乘虚而入,利用蒋介石多疑的心里,制造谣言与事端,以进一步挑起蒋介石与汪精卫,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”,未免本末倒置。明明是蒋在日记中无端指控共产党挑拨:“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,回寓宴客,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,其欲陷害本党,篡夺革命之心,早已路人皆知。若不于此当机立断,何以救党?何以自救?乃决心牺牲个人,不顾一切,誓报党国,竟夕与各干部密议,至四时,诣经理处,下定变各令。”蒋于事发当晚,还去汪府探视,留下一段日记,“傍晚,访汪病,见其怒气犹未息也”。
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未删原文是,“见其怒气冲天,感情冲动,不可一世。因叹曰,政治势力恶劣,至于此极,尚何信义之可言乎”。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,与被害人相见,不显露窘态已属罕见,哪可能“怒气冲天”、“不可一世”?接下去一句则更值得玩味,无异于蒋氏承认,因为“政治势力恶劣”,就可以不讲道义。汪之所以“怒气冲天,感情冲动”,岂不即因蒋不讲道义?蒋在日记中居然如此颠倒,将自己由加害人伪装成被害人,他日记中的中山舰事件还有可能是真相吗?完全不可能!其中颇多他故意扭曲的真相,目的在于误导世人。
其二,西安事变的真相在蒋日记里吗?显然不是。《西安半月记》根本不是蒋在西安期间的日记,而是事后出自陈布雷之手。除陈自述外,蒋也透露他本人曾据陈布雷撰写的《西安半月记》继续修改日记。他在1937年2月12日记道:“晚修订西安半月记。”翌日又记曰:“上午修正半月记完。”实则尚未完,隔了两天,于2月15日又说,“改正半月记甚费力也……夜以修正半月记未妥,几不成寐也”,足见他煞费苦心在事后建构他自以为是的西安事变。他刻意修饰,必然为扭曲事实,以至于《西安半月记》被改得面目全非,无非为颜面掩盖真相。
其实,早在当年事发后傅斯年的密函中,真相已基本呈现:(1)蒋确与周恩来在西安见过两次面,并答应不剿共,中共方面也因抗日答应红军接受中央指挥。蒋更保证今后不再进剿红军,而且可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。此已可确证蒋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有承诺在先。然而在1956年出版的《苏俄在中国》一书中,虽有陶希圣等人执笔,蒋仍要亲笔增补,谎称“我们终于无条件的脱险回京”。(2)蒋之被释放,确实由中共方面主持方得实现;傅氏特加括号注明:此事亦已证实,并且说,“共党之主张放蒋,坚谓不赞成张之扣蒋是事实”。(3)蒋在西安虽未签字,但确曾口头同意。傅氏据西安友人谓,“西安遍传蒋云终身不内战”。(4)蒋回南京后,不仅未如约撤兵,反而增兵。傅氏写道,“又有确切消息,除原有军队未撤外,又运去六师连夜前往,我听这消息大为兴奋”。(5)张学良在受审时,确有强烈表现,傅氏说,“张作一个政治演说,大骂南京政府及蒋先生左右,自何(应钦)至政学系,银行家等等谓蒋好而南京太坏,彼如在一日,必拥护蒋,亦必打倒南京政府云云,此演说把审判长greatly
impressed(大大地感动了)。事为generalissimo(委员长)所闻,甚气,谓不放这小子回去!所谓管束有三端,即居处、见客、通信皆不得自由也”。此外,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的动机,纯为逼蒋抗日以救国已无可疑,但事变后20年,蒋介石在《苏俄在中国》一书中,虽已无《西安半月记》所谓张学良之转变系因看到蒋日记的“神话”,但仍不承认答应任何条件,说张学良是在其八项主张被拒,南京下令讨伐,才决定将其释放。蒋甚至借宋美龄之口,将其西安“蒙难”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。由此可见,蒋要我们知道的西安事变,绝非历史真相。
其三,蒋在西安事变后转变对日方针,胜利后成为英雄,汪精卫因公开降日成为汉奸,孰知战后日方公布或泄露出来的文件,证明蒋日之间也有不少秘密接触。唯一不同的是,汪是明通日本,而蒋则暗通日本。蒋介石一直宣传抗日到底,在日记里还说日本向他求和,而他严词拒绝云云,无非想要掩藏通敌的暗盘。读史者若以日记为据,证明蒋阻止或拒绝和谈,即被蒋所骗。蒋难道会在日记里留下为后世骂名的痕迹?他的日记故作义正辞严,留给后人看而已。他在194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说,“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伪状以欺敌人,敌人信之”,但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明明是代表蒋方之人,蒋却将张之所为公然嫁祸于“汪奸”,显然又是欺蒙世人的谎言。蒋在日记里说,日本向他求和八个月没有效果,他没有授权任何人和谈,委任状是由别人伪造。读蒋日记者,若轻易信之,无异于盲从。
其四,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美苏的支持下,策划重庆会谈。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自延安来重庆,名为共商大计,实要逼毛就范,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名,要求中共交出政权与军权。他以为有美、苏两大强权支持,凭其政治优势与军事实力,再以“宽大待遇”,就可“解决”中共。毛泽东决定接受邀请赴渝,蒋以为得计,于1945年8月31日记下,“毛泽东果应召来渝,此毛应邀前来,虽为德威所致,而实上帝所赐也”。但是两人会谈并不顺利,蒋欲“招抚”不成,情绪益发激动,在日记里发泄,出语不逊,想要“扣留”毛泽东。如果把蒋日记里的这些气话当真,就是不幸地被日记牵着鼻子走了。因为在美、苏的保证与国际的众目睽睽下,蒋若“扣留”或“审治”毛,必然会动摇他在国内外的合法地位,所以他不能也不敢像扣留和审治张学良那样做,实因风险太大,代价难以承担。所以读蒋介石日记,不能随其起舞,而应洞见其复杂的心思。
蒋氏日记对上述四大关键史事的认知,毫无助益,不见其真,反见其伪。我们不禁要问,大量的蒋氏日记,材料丰富,牵涉甚广,其中到底有何精彩的发现,可发百年之覆呢?似乎没有。日记不是没有颜色的史料,其中有情绪、主观、偏见、谎言,更有不切实际的异想。谁也不能保证日记里没有“骗人”的话、自恋的话,更没有人能保证日记里所说的、所以为然的、所判断的都是正确的,想做的事都能落实。日记是可贵的史料,但引用者必须加以分析、研判,检视与日记作者同时代人的看法,尤其是与他接近之人的看法,并参考当时的政治、社会与思想氛围,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,不能偏听偏信。我们引用蒋之日记,如果不假思索,一味抄录、编排、复述,被他所说左右,随其情绪起伏,则要史家何用?
其实,引用任何日记都必须注意其中有“鬼”,既有“不立文字”以自讳其迹,也有“专立文字”以自我掩饰。所谓“不立文字”,就是口头答应,而不立下字据,如“何梅协定”、西安事变各方商谈结果,都是口头答应,皆未立文字,故而不留痕迹;而所谓“专立文字”,就是虽白纸黑字表述明白,却是不能兑现或故意留给后人看的材料。例如蒋介石批准释放军事家蒋百里,事实上仍旧关着;又如蒋介石骂史迪威的批示,史迪威看不到,是留给史家看的。
“档案”中的文字,有的就难称历史事实,“只是专门用来骗人的,尤其用来骗后来之人和历史家”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斯(natalie z.
davis)在《档案中的虚构》中提出,16世纪法国司法部的赎罪档案所载故事纯属虚构,史家不可据此以重建历史。读者如果被材料牵着鼻子走,就如跳进如来佛的掌心而不得翻身。档案尚且如此,何况日记?我们引用包括日记在内的任何史料,若不细察其中的狡猾处,则所得之所谓真相,不过是镜花水月而已。蒋在日记中大谈宋明理学,以修身养心、自我勉励。读者如据此相信他是“一个新儒家青年”,遂下结论: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“自律”与“品格的培养”,便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、很勇敢、讲荣誉、非常积极之人,则是随蒋起舞的莽汉。
须知,蒋介石日记不同于一般人的日记,不仅仅是其个人在一日空间里的“自说自话”,更不是他个人的私密空间。他写日记作为反省与励志,经常提醒自己“知耻”成常态,显然效果不彰,反而令人觉得是无感的俗套。他“知耻”了吗?好像没有,不然何以一败涂地?他检讨自己,语焉不详,但骂别人十分具体而恶毒,甚至离谱。他说胆大包天的张学良“怕死胆小,狡猾糊涂”;他指责陆军总司令孙立人是“匪谍”;他痛斥驻美大使叶公超是“汉奸”,都是口不择言、虚妄不实的话。
蒋介石日记最大的用处,应该是从他的每日所记之中,细察他有意或无意透露出来的内心世界,以便深入分析他的性格,作为分析史事的一定依凭。他从小在乡里就有“瑞元无赖”的绰号,论者多不以为意,认为是年少轻狂,但他的无赖性格在后来的诸多行事中时而复现。无赖或流氓若有气度,未尝不能成为有为之主。无奈蒋介石的无赖与心胸狭窄兼而有之,例不胜举。如他谎报“日本士官学校毕业”,显示他在心理上缺少安全感;他为了与宋美龄结婚,骗妻子陈洁如出国5年,随即悍然否认与陈存有婚约,显示他毫无信义;他押禁张学良,终其一生不肯释张,显然是背信与毫无气度之举;他捉弄李宗仁,甚至在就职典礼上,在着装上占尽李的小便宜;他将“外蒙入会案”的失败甩锅给叶公超,骗他回台北,软禁终生。做这些事的蒋介石,岂不很无赖吗?读蒋日记者,能不慎乎?
〔作者:汪荣祖/中国近代史学家 原载:《历史评论》2021年第1期〕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