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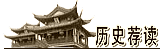 |
访唐山:追思与感悟 |
|
原标题:唐山大地震:一块整钢,还是一盘散沙?
文/郭松民 来源:作者博客 2016年07月27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
| |
|
【核心提示】今天的时代焦虑是什么?简言之就是去组织化,就是各人顾各人,就是孤独和无助。……假如明天地震或别的什么灾难来袭,我们是像四十年前的唐山那样,团结成一块整钢,还是像当今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的李元妮那样孤独无助?是到了认真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 |
| |
|
2016年7月14日,我第一次来到唐山,就惊讶于她的恢弘气势和蓬勃生机。
1976年7月28日以后,唐山以“大地震”定格在很多国人的心中。但震后四十年,唐山完成了凤凰涅磐,经历十年重建、十年振兴、二十年快速发展,再次成为渤海之滨一颗耀眼的工业明珠!

在唐山抗震纪念馆,我们向刻有24万遇难者名字的黑色大理石墙默哀。40年前的灾难来势极为凶猛,以至于我们在纪念广场上面对保留下来的废墟时,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可怕与狰狞。

但是,更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,如此巨大的灾难却并没有战胜唐山人,而唐山人却迅速战胜了地震:震后七天组装出第一批自行车;震后十天生产出第一车煤;震后十四天发电厂开始发电;震后二十天造出第一台机车;震后二十八天炼出第一炉钢……
泰山压顶不弯腰──对唐山人来说,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豪言壮语,而是一个简单的事实。
唐山人为什么如此不可战胜?也许,发生在地震中的这样两件事,能够向我们揭示其中的答案。
第一件事发生在开滦煤矿。在大地震发生时,开滦的吕家坨矿正在进行高产突击活动,井下共有1006人,其中有100多名机关干部,还有兄弟单位的打井队、参加大会战的洗煤厂工人、下井不足半个月的新工人,还有四十几名女同志,职务最高的是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。
地震发生后,井下迅速成立临时党支部作为团结和指挥中心,由贾邦友担任书记。他宣布了撤退顺序:女同志先走,兄弟单位的同志先走,然后是井上工人、采煤工人,最后是机关干部。
近5个小时的撤离,紧张、安静、井然有序,撤退途中,需要经过一段九十多米长的梯子上,每次只能上一个人,一千多人要从这里通过,稍有混乱,后果就不堪设想,但是没有发生任何混乱。
贾邦友就像是传说中海难发生时最后弃船的老船长,在所有人都升井后才返回地面。他发现先上井的人并没有跑回自己的家,都在余震中焦急地等待井下的同伴,也在准备应对新的险情。贾邦友心里一阵发热,赶紧说:“矿上不要管了,都回家看看吧。”

第二件事发生在震后不到30分钟,一辆红色救护车从唐山矿出发,向北京驶去。这是唐山市第一辆“苏醒”的汽车,车上是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他的三位同事,在没有任何人向他下达指令的情况下,李玉林主动想到唐山和北京之间的联系可能已经完全中断,要尽快向中央报告,只有中央才能救唐山。他们飞车四个多小时赶到中南海,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人纪登奎、李先念、陈锡联、陈永贵、吴桂贤等立即接见了李玉林,并在几分钟内就做出了调解放军、调医疗队、调各地井下救援队开赴灾区的决定,为救援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。
李玉林在飞车赴北京的途中,和三位同事组成了临时党小组,相约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确保把灾情迅速报告中央。沿途不断有市民、农民拦车让他们抢救伤员,但一听说他们是要到北京向党中央、毛主席报告,就全力配合,主动移开路上倒伏的树木、电线杆和伤员,为他们扫清道路。

这两件事,足够让我们找到唐山战胜地震的原因:依靠组织,相信中央。党员是群众中最有威信、最有责任感、最有能力的人。群众信任他们,他们也无愧群众的信任。无论是在大地深处还是在废墟之中,无论发生这样猝不及防紧急情况,只要有党员,组织立刻就可以重建。百万人口的唐山,没有在大地震的突袭下溃散,反而结成了一个具有高度韧性、高度效率的有机体,成了一块摧不垮、打不烂、压不扁的整钢。
可以相信组织的力量,唐山人就不相信眼泪。一位当年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后来回忆,部队开进唐山后,最让他惊奇的是“唐山发生了这么大的地震,居然没有哭声。”幸存的市民有的继续寻找被埋的亲人,有的照顾伤者,有的起火做饭提供后勤保障,还有的在搭防震棚,气氛凝重,但不压抑,忙碌,但有序。

唐山人并不是真的不会哭,一个多月后,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传来,唐山哭成了泪城!他们把失去亲人的悲痛,和遭受了“无法弥补的损失”后的隐忧与无助,都一起宣泄出来了。
在唐山,我想起了冯小刚导演的《唐山大地震》。2010年,这部电影上映时,赚取了不少眼泪,也收获了5亿多票房。
但透过这部电影,观众却只会觉得是地震战胜了唐山人──他们的生活不仅当时被地震摧毁,此后也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不是吗?李元妮一生生活在对亲人的歉疚中了,如同儿子方达所言:“倒塌的房子都盖起来了,可我妈心里的房子永远盖不起来,三十二年守着废墟过日子。”方达永远失去了一支胳膊,方登则生活在被遗弃的恐惧与怨毒中,始终无法化解,连累无私收养她的养父母也活的郁郁寡欢,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方登,却无法在她那里得到一个笑脸。
通观整部影片,冯小刚几乎删除了全部时代及地域因素(除了徐帆一口不标准的唐山话),他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唐山大地震,拍成了一场“抽象的灾难”──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,比如印度孟买或美国新奥尔良。从电影中,你看不出救援和灾后重建有任何时代特征。党组织呢?没有。单位领导呢?没有。街道居委会呢?也没有。解放军倒是出现了,但他们要么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跑来跑去,要么为时过晚地乘直升飞机从空中掠过,和卡特里娜飓风中的美军区别在哪里呢?看不出来。
电影的确令许多人留下了眼泪,流泪的人或许都在潜意识中联想到了现实中的自己。实际上,《唐山大地震》并不是源于历史的真实,而是出自现实的投射。说到底,每个时代能够打动人心的文艺作品,反映的都是特有的“时代焦虑”。
今天的时代焦虑是什么?简言之就是去组织化,就是各人顾各人,就是孤独和无助。
几十年来,从小岗村分田单干到国企减员增效,一路走来,唐山大地震时高度有效、“粘性”极高的基层组织,在很多地方已不复存在或形同虚设,以党员为核心的自组织能力,也被遗忘的一干二净,更令人担忧的是,党员、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那种高度的相互信赖,很多时候也消失殆尽了。
为什么会这样?腐败,是一个原因。群众对组织的无条件信任被透支,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潮中,一些多年的劳动模范,被动员率先下岗,理由是国企遇到了困难。遇到困难不是团结群众一起克服困难,而是把群众抛弃,还会有比这些更有效地摧毁群众的信任吗?试想当地震发生时,贾邦友和井下的一百多名党员干部不是组织大家有序撤离,而是自己率先逃命,吕家坨矿的井下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?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同样是冯小刚导演的宣扬“组织不可信”的《集结号》才会风靡一时。如果我们把《集结号》视为九十年代以来社会现实的一种折射的话,那《唐山大地震》倒也能堪称是一部“现实主义”的力作。只不过这个“现实”是距离真实的唐山大地震之后三十多年的现实。
最近一些日子,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洪灾。我们听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,但也有些故事听过以后令人揪心。
旧中国时,中华民族曾经是一盘散沙,新中国成立后,在毛主席的领导下,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,曾经把全国人民团结的像一个人。但今天,重返一盘散沙的可能性再次严重出现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强调“不忘初心”,可谓切中时弊!

今天的中国,最紧迫的已经不再是gdp或招商引资,而是重建社会共同体,重建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的社会团结,重建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。这需要党再次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,党员干部再次践行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的原则,灾难来临时要像贾邦友那样把生的希望让给工人,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
假如明天地震或别的什么灾难来袭,我们是像四十年前的唐山那样,团结成一块整钢,还是像当今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中的李元妮那样孤独无助?是到了认真想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。
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