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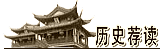 |
鲜为人知的华工“一战”故事 |
|
文/记者 田毅 来源:观察者网 2014年07月31日 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
| |
|
【编者按】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。一战期间,有14万中国劳工远渡重洋去往欧洲前线,承担了最艰苦、最繁重的战勤任务,1917年中国政府宣布参战后,华工被直接派往前线。一战华工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取得战胜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,对世界经济、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成长,其作用都不容忽视。然而,善良朴实的中国劳工在为协约国流血流汗之时,却遭到了英法军残忍的虐待。 |
| |
|
百年前,中国农民不远万里遭遇一战中的飞机、大炮,被炸伤乃至吓疯,这充满隐喻。稍许的兴奋,更多的是惊恐,仿佛也是百年来传统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心态之一种。
1918年5月23日晚,法国西北部小镇努瓦耶勒(noyelles),如往常一样寂静。这里距巴黎200公里,正在英吉利海峡中段,与英国隔海相望。大西洋在此深入陆地形成一个小小三角,零星的湖潭则继续向三角尖所指的土地延伸,仿佛洒在小镇上的颗颗水珠。大片麦田,条条土路,低矮密集的树林……
入夜,不及12点,小镇西南端突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,一声接着一声,大地随之颤动起来。火光迅速向天空升腾,红的、紫的,闪亮刺眼。
原来,趁夜,德军飞机将炸弹投向小镇的赛涅维勒村(saigneville),这里有着英军在法最大的弹药库,它与努瓦耶勒镇中心及一战英国军营正好呈三角形,各自约十公里。
小镇上,英军军营被震撼着,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不断传出。
严格说,这里并非真正的军营,而是“一战华工总部”。新民国政府急于参战,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活命无门,自1916年开始,14万中国农民“以工代兵”漂洋过海,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。此刻,欧洲工业文明正盛,亦是热兵器枪炮激烈对抗的大战之时。在中国的千年历史上,从来没有过如此众多的农民走出贫苦的家舍,集体跑到地球的另一端。他们大多数只知道要“做工”,赚现洋养家糊口,但对做什么样的工与“一战”一无所知。
14万华工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到过努瓦耶勒小镇,或中转到比法前线,或在法国内地。小镇常驻华工最多时竟超过12000人,成为欧洲最大的华工营地,而这里原居民不足千人。
小镇来了挑扁担的中国人
1916年6月,小镇居民割完小麦,英国人就开始建设第一块营地了。几次扩建,总面积达到30英亩。
10个月后,努瓦耶勒居民惊讶地看到第一批中国人从火车上下来,由手持粗木棍的英国士兵严密看管。joseph de
valicourt当时还是一个爱凑热闹的小伙子,他观察着这群个头不高的中国人,“穿着蓝色的大棉袄,带个小圆帽和毛耳罩,缠着绑腿,灯笼裤。手上带着身份识别的编号铜手环。他们的竹竿(扁担)挑着米袋、木板,前后晃悠,还有一个大轮子架着三角把手的独轮车。这些外来者的气色非常差,但纪律严格。”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。
这群平生摸惯了农具、从未跨出国门甚至很少到县城的中国农民,在往来穿梭的军人、川流不息的现代车队、完全陌生的炮群中,显得格格不入。
不过,当他们在异地看到熟悉的农田时,joseph de
valicourt发现这些黄种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相对于恐怖而漫长的旅程来说,土地给了他们安慰。
之前,镇上居民听说他们将带来“地球那端的一种文明”,如今这种新鲜的文明被送入铁丝网中的营地。
营地呈四方形,两层带刺的铁丝网在最外围,有英国士兵荷枪实弹,“像牧羊犬一样来回巡逻”。第一层铁丝网一人多高,第二层至少两人高,间隔七八米就有木栅栏。营地分成若干小方块,每个区域还有铁丝网,里面是几顶大帐篷与二十几个小帐篷。华工营中间,有几大丛不高的树木,像一堵堵小墙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想逃走,至少要翻过三层铁丝网,还得保证子弹不击中你。
铁丝网里集中着工棚、厨房、食堂、厕所、医院甚至监狱,还有那座后来设立的疯人院——走过住宿区,穿过这些树墙,营地那端靠近铁丝网尽头,就是疯人院了。
“sani-mama!sani-mama!”
睡梦中的华工被爆炸惊醒后,很多趴在地上叫喊、磕头。他们一生中听到的最大声响不过是鞭炮或锣鼓。
爆炸越来越近,一架飞机轰鸣着掠过他们帐篷的木顶,巨大的气浪掀翻屋顶,他们无处可藏,尖叫着开始拼命向外狂奔,向铁丝网冲去——
按出洋前签订的合同,华工不是战斗编制,应享受工作之外的自由,而现实远非如此。劳工营的拱形大门一到晚上就关闭了。按英国人规定,除了做工,华工走出大门的机会很少,幸运者回来时的通行证会被立即撕掉。
几十年后,小镇居民多米尼克·德拉努瓦(dominique
delannoy)还清晰地向当地报刊记者描绘华工推着“奇怪独轮车”的样子,有不少人就这样穿梭于火车站与军营之间,仿佛还在华北乡村一样。战争期间,他们冒着枪林弹雨,挖掘了数千公里的战壕;他们背负一二百斤重的弹药箱、军粮以及引信不稳定的大口径高爆炮弹;他们还装卸物资,甚至继续种粮种菜保障供给;激战后,参战国士兵各自回家,但华工不得不留下清理成千上万的残留炸弹和尸体。
华工的另一个重任是铺铁路,不远处就是一战第二大枢纽。从本刊获得的当时照片上看,华工先要用铁锹挖出宽20米左右、一人深的路槽,然后夯实,再铺上枕木、铁轨。
“sani-mama!sani-mama!”此刻,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冲向铁丝网的华工不断如此大叫。听到的小镇居民不知其意。
大家的狂奔没有方向,但必须先突破那三层铁丝网。从当时铁丝网的照片上看,如果多人用力很可能推倒木栅栏,情急之下,也可能直接以手拉开铁丝网拼命钻过去。
在跨越铁丝网的那个瞬间,那些华工不仅仅带着对轰炸,对庞大“怪兽”飞机的惊恐,他们身上还有某种耻辱,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想逃离“努瓦耶勒地狱”。
每天要工作10-16个小时,不准随便说话随便活动;如果有华工表现出不够顺从,甚至是稍有敌意,立刻就要遭到英国军官的一阵皮鞭毒打,甚至关入监狱。英国人称他们为coolie(苦力),事实上更类似于战争奴隶。
逃离“努瓦耶勒地狱”
1970年当地记者roger
pruvost采访了若干位亲见一战华工的努瓦耶勒居民,本刊试图寻找这位记者,遗憾的是他已于去年离世,本刊从小镇获得的原始资料显示,居民纳塔莉·萨勒(nataly
salle)夫人告诉roger:
“先生,那真恐怖!我们看到英国看守像打狗一样殴打他们。把他们的鞋子、衣服全部脱掉,绑在桌子上,一直鞭打他们直至流血。接下来,英国人用刷子和热水将他们擦干净,不留痕迹。然后人们将他们送往劳工医院。我对您说,这很可怕。有的人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,我见过一个人被绑在对面那棵树上,被牛筋鞭残忍地抽打,当人们解开他时,他倒了下去……他死了。”
华工医院由苏格兰人格林(gray)负责,他在1918年1月的一封密函里为华工打抱不平,“任何一点纠纷,英国军官不明就里,便粗暴地命令士兵开枪”,“军官们似乎非常害怕华工,收工后将华工限制在铁丝网内”。相对法国人对华工的宽松,英国军人显得非常过分,这主要源自他们对华人的鄙视,认为他们是“食人族”、“chink”(中国佬,侮辱性称呼),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之劣根性,“你对他们越好他们就越不买账”。
有的华工实在无法忍受虐待,又不想执行非人道“自杀性任务”(如排雷),便在华工营房里挖一个地洞,将自己埋进去自杀——好歹留得全尸,将来魂灵才能回到故乡。
当时在欧华工中流传着一句话:谁不听话,就会被送到“英雄队”去!“英雄队”指的正是努瓦耶勒华工营。如此之地,逃跑也许早就在华工心中酝酿了,借着这次飞机轰炸,能否远远离去呢?
“sani-mama!sani-mama!”华工们惊叫着倒在血泊中,或者眼见身边同胞喋血。
无论是遥远故乡祖祖辈辈农耕日子的平静,还是初到异国的新奇,甚至那些在努瓦耶勒不人道华工营中的经历,其印记也许都无法与这些“怪物”的巨响与杀伤力相提并论。
有记载说,初次在营地或前线看到飞机掠过,华工很好奇,甚至从掩体里跑出来张望,结果被炸死炸伤不少。“一些穿着蓝色衣服的中国人因为害怕飞机的轰炸……就疯了。”英国墓地委员会向本刊提供的一份资料里,一位亲历者如是写道。当时一位中国翻译黄道荣曾描绘了德国飞机的“经常光顾”:有一次,一架德国飞机毫无目标地向华工驻地投了一颗炸弹,正落在一间住房旁,整个房间被炸毁,死伤华工20多人;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《北洋政府档案》中也有提及,“(一些)害怕德军飞机轰炸的华工遂离开工厂,成为‘黑号’。”可见华工对德军飞机之恐惧。后来,一些学者在访问一战华工时也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,他们中很多人对“飞机”一词避而不谈,只说“轰炸”,似乎在有选择地记忆或忘记。
这样的怪物其实在中国被发明实验比莱特兄弟晚不了几年,甚至清末在北京南苑还设立了机场与制造厂,但完全没有应用,更别说被普通农民见到了。而在欧洲,飞机迅速应用到战争中,从侦查对方甚至高空互打招呼,到安装机枪,携带炸弹,几年间大大提升。
百年前,中国农民不远万里遭遇一战中的飞机、大炮,被炸伤乃至吓疯,这充满隐喻。稍许的兴奋,更多的是惊恐,仿佛也是百年来传统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心态之一种。
“疯人四方院”
努瓦耶勒的华工们突破了一道道铁丝网,除了被德国飞机炸死的,一些华工终于在没有英国监工的情况下站在铁丝网之外的世界。当然,他们不能停留,必须快跑,不论是躲避炮弹,还是趁机逃离。
他们穿过田野。
几个小镇居民当时看到了他们的奔跑。他们对这些中国人的了解不多。一个印象是他们极爱吃苹果(华工多来自山东,那里出产苹果),初来时甚至不惜用一天的工钱买一个苹果。后来,他们学会了用手势砍价。最熟悉的身影要算那两个打扫小镇街道的华工,冬天,扫完地,他们总是安安静静地在一个铁匠铺里取暖;他们也会去杂货店,小店有时会向中国人卖出积压多年的货物。简单交流时,这些外来的黄种人总是笑着说“是”或“不是”。
有法国人称这些华工“非常幼稚”,甚至把很多坏事安在他们身上,但也有人说他们极其善良,比如自从华工打扫小镇后,就变得异常干净。到了战后,英国人对华工管理没那么严格,个别赌博、偷窃的就有了,还有的晚上翻出铁丝网去找法国妇女。
轰炸之下,华工继续向树林奔跑。他们竭力将军营抛在脑后,将疯人院抛在脑后。我们不清楚此刻疯人院里的中国人的反应,他们是否也拼力夺路而逃?还是龟缩在一角在恐惧中等待?
这里后来被称作“疯人四方院”,在华工营中被隔离开,平常许多小镇居民都隔着带刺的铁丝网远远地见过他们——有的昏倒在地,有的则痴呆地立着。
除了被飞机轰炸弄得神志不清甚至发疯,第二大刺激源是战场收尸,或是看到同胞触雷而死。一篇文章描绘了一次战役后战场的情形:“放眼望去,满地都是破枪、碎片、头盔衣物,令人感觉恐怖。”
还有一种原因是思念。据一位研究者valicourt的文章,有名中国监工,在国内由于生计所迫,一意孤行来到法国,妻子苦劝无果,在国内悲愤自杀,噩耗传来,他悔恨交加,最后精神失常,被送进疯人院。
“我无法解释,”外国人士frederickstrange如此说,“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劳工在法国疯了?”最新出版的《一战华工》一书的作者gregory
james教授分析道,“劳工自己把同胞身上这种无法修复的精神疾病归咎于巨大的惊吓,或者‘对空中狂轰滥炸的恐惧及其后遗症’,虽然欧洲人愿意认为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劳工本身就是意志薄弱的‘乡下人’,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。”
我们尚不清楚1918年5月23日晚德军飞机轰炸时,努瓦耶勒华工疯人院里的华工具体数量及发疯原因,查询的英国墓地管理委员会及法国当地档案中都没发现相关记录。
惊恐万分的华工们继续穿越田野,那里原本是麦田,百年后的今天,营地的痕迹早已消失不见,取而代之的依然是一大片麦田。在华工医院旧址,记者只发现小树林里那块长满青苔的水泥板。
如今,在这片树林中,现在竖立着840余座华工墓碑,每座都面朝东方——他们的家。他们中有被炸死的,有病死的(特别是1918年席卷欧洲的那场伤寒),也有的积劳而死,当然还有的疯后死去。
战后伊始,包括疯人院的死者等华工尸体非常杂乱,有小镇居民甚至看到尸体被一个挨一个竖立着草草埋下。后来墓地重修,但很多碑下并无尸骨。而据纳塔莉·萨勒夫人当年告诉记者的,“墓地里死去的八百多人中,有一半是疯掉后去世。”不知这个说法是否存在夸张,但遭遇恐怖惊吓与思乡成疾而疯了的华工为数不少。
这些中国人在这里留下的档案少之又少,没人在意他们。“谁派你过来的?”本刊记者采访时,市长助理加里尼米歇尔的表妹问了好几遍。最后一次,她又问了一遍:真的没人叫你过来找我们吗?记者说,如果实在要说有人,那就是上帝好了。他们笑了。
带“烟囱”的中国旱船
轰炸、非人管制之下,华工也不是没有快乐时光,只是片刻而已。
就在这次轰炸前的3个多月,1918年2月11日,努瓦耶勒街道上人山人海,欢腾无比,华工们被允许在这个中国传统春节时走出营地欢庆。在一或两层,方底尖顶、有小阁楼、有烟囱的一幢幢法国民居间,在不高,光秃秃的树木下,百人、千人汇集成一簇簇围着社火的队伍。
他们大多是头戴毡帽,身穿旧大衣的华工——其中不少人正对着站在高处的摄影师的镜头好奇遥望或憨笑。当地居民散在人群中,一身军装头戴大檐帽的英国军官最靠近社火——中国式鼓乐齐鸣中,两艘“旱船”鱼贯而来,后面跟着舞龙与高跷队。
旱船以竹竿与布扎成,一人船内撑船摇摆,一人船外相引,走在前面的引船男子上身大花袄,头戴大花,手捏彩布,脚蹬圆口布鞋。百年后,面对照片,一个细节让本刊记者很是惊奇,几艘旱船前后左右各粘着一个不高的长方体,中空,这在中国旱船里非常少见,让人一下子想到那是否代表着轮船的“烟囱”?他们就是乘着如是代表西方大工业文明之船,在烟囱的滚滚黑烟中,渡海而来。
提灯游行、唱京戏、听说书、民国五色旗前列队拱手互致大吉,甚至有人在营地里搭起一座一人多高的小庙,挂起幡子,双膝跪地,双手合十,拜了又拜……那一天华工似乎回到了中国。
3个月后,1918年5月23日,在那个炮火轰鸣的夜晚,这群曾在锣鼓中欢笑着的华工,惨烈死去或逃出铁丝网。他们叫喊着钻进密密的树林,他们曾经还在这里伐木,他们想跑得远远的。1918年5月24日,德军飞机轰炸的第二天,英国军人开始搜寻。
没人知道森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几天几夜过去,那些跑入森林的华工才被英国人陆续被发现——他们中大部分已饿死或冻死,活着的人中很多已神志不清,他们被押回小镇华工营,送进层层铁丝网后面的那座疯人院。
1918年9月20日,一批华工从法国马赛港乘船踏上归途。据《一战华工》作者gregory
james教授引用的资料,船上1/3的人患有精神疾病。
1919年4月28日,当轮船抵达青岛时,有85人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。患有精神疾病的劳工中,有3位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被暂时押到宪兵站的牢房;还有一些“抑郁”以及不能连贯说话的轻度患者,被人看护起来等待他们的亲戚来接。
从时间上看,这艘船运送的伤病华工发生在努瓦耶勒被轰炸后4个月,努瓦耶勒疯人院的“幸存者”,是否也会随船归来?
华工回到青岛后,重新散入20世纪初的那个中国。没能回国的疯人院华工及其他死去的同伴日后被就地埋下,当地人称他们是“天之子”(fils
du
ciel)。受尽苦难的“战争奴隶”,为何得到这样的称谓?是“天堂之子”的意思吗?他们死在那里,无声无息了。也许,在法国人眼中,这些和战争无关的中国人,仿佛是老天派来的,然后老天再将其中的死者收去。
百年后,记者来到这里,每个华工墓碑下,都有些英国小玫瑰点缀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升向努瓦耶勒的天空。
(特约撰稿 张鑫明 张小夏 白玉 记者 田毅/文)
|